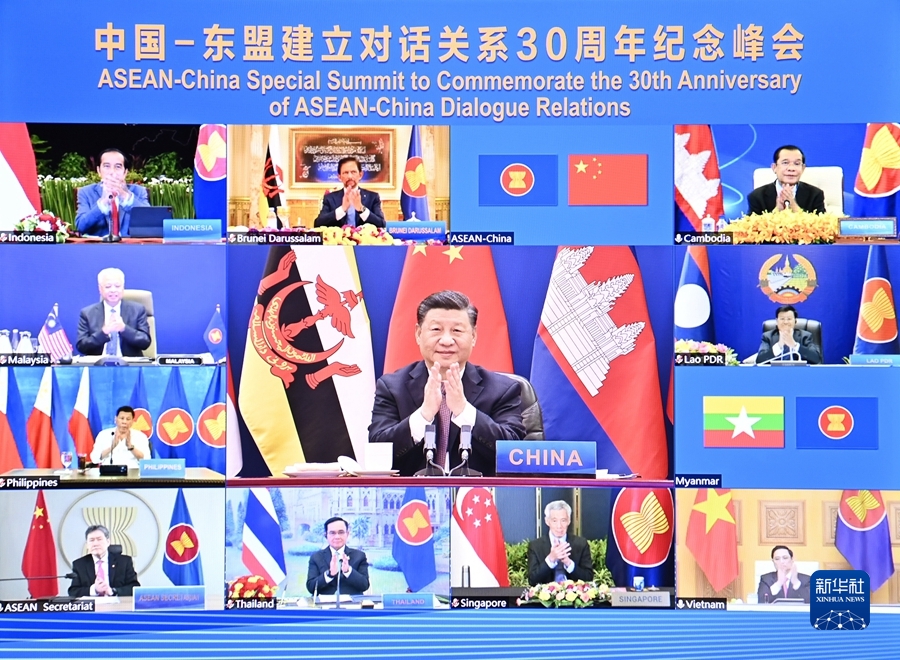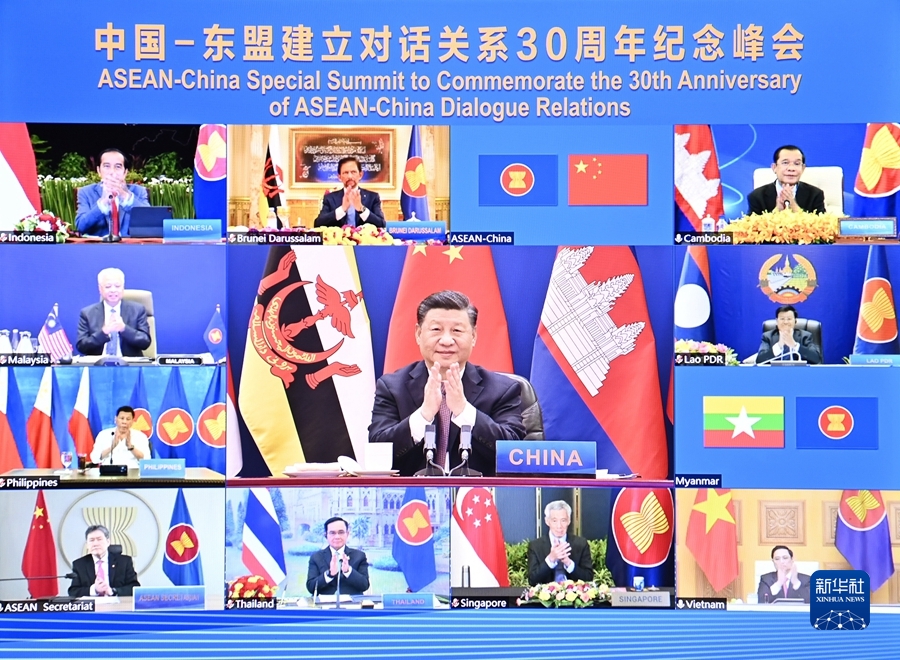|
中国和东盟的知识界如何超越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彼此,共同合作发展出一套有利于双方友好合作的知识体系,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和挑战。双边合作既需要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性企业家来推动和引导,也需要学者积极为双边对话合作提出引领性的观念和知识。
然而,我们过去在认识彼此的时候,多多少少太倚重西方关于东南亚学和中国学的知识,从而潜在地影响了我们对彼此的判断和认识。这么说并非要否定西方过去关于东南亚和中国的知识,而是说这套知识体系存在不少问题。我来印尼的时候,在上海飞往雅加达的飞机上读一本东南亚历史的书,是西方人写的,作为一名学者,我的知识面使得我在阅读的时候能够对书中关于东南亚偏见性的知识保持警惕和鉴别。在阅读的时候我想,如果普通读者阅读的时候,恐怕不会作必要的警惕和鉴别。假如全盘接受的话,其对东南亚的认识自然会受这类历史书的影响。
爱德华·萨伊德批评了西方关于中东的研究,是戴着西方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的眼镜来研究中东的,有关中东的知识存在很多误读和偏见,他将这种偏见性的知识称为“东方学”。实际上,也许我们可以说西方也存在一个东南亚学,这个东南亚学当然也是戴着它们的眼镜得出的。同样,西方也存在一个中国学。现在东南亚和中国的知识交流状况是,你们东南亚学者更多地依靠西方生产的中国学来认识中国,在我们中国,学者一定程度上也依靠英语世界关于东南亚的知识来认识东南亚。这就是知识交流的一个尴尬的现状,我们需要打破这个现状,转到更多地彼此合作,立足自己,形成关于彼此较为准确的知识,从而为双边合作构筑更为客观的知识体系。
举个例子,东南亚学者受到费正清的朝贡体系影响不小。然而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用“朝贡体系”这个概念来认识过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这个概念使用日久,使周边国家潜意识担心中国强大后会恢复这种体系。然而,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过去同周边地区形成的是大小国家共生的体系,是一个共生秩序,不是费正清误读的朝贡体系。同样,我们研究东南亚,根据西方提供的东南亚学,可能觉得东南亚是一个野蛮、未开化、愚昧的地区,然而,东南亚的文明和历史非常久远,在人类文明史中同样贡献很大,所以东南亚国家学者也需要对这类知识进行必要的清理,写出自身卓越的历史来。
那么,我们如何超越西方生产的东南亚学和中国学,形成双方持久合作的知识基础,来真正加深彼此的认识和理解?这需要双方知识界的自觉和思想解放,通过人文交流,共同合作,逐步形成我们自己双边合作的知识体系。
我认为,双方已经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从中国外交哲学来讲,我们在对待区域合作问题上,强调合而治之,我们支持东南亚走符合自身区情的合而治之道路,支持东盟扮演核心作用。我认为这个外交哲学需要大家共同去研究和发挥,假如我们不加鉴别地奉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而治之”为圭臬,我们双边合作以及东盟内部合作必定会出问题,各位知道,分而治之这种殖民主义外交哲学思想和遗产对世界许多地区造成了也正在造成很多痛苦和悲剧,中国外交哲学和外交价值观不接受这套理念,我们对各个地区的合作都持“合而治之”的哲学和价值观。我们对非洲、拉美、阿拉伯国家、中东欧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奉行的都是这套合而治之的外交哲学。
同样,东盟也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自己的实践和知识。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概念,我个人认为比欧洲一体化概念要更适合东盟地区发展以及东盟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也倡导互联互通概念。东盟应该有智慧,超越和避免欧盟进程中的问题,形成自己互联互通的道路,我个人认为,我们与其按照欧洲一体化理论来对照自己的发展,还不如切实以互联互通理论来探索出发展中地区区域合作的新路来。在这方面,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工作可以在各个层面、环节、领域来逐步推动。
这方面有利于促进彼此合作的共同知识生产还有很多。比如,东盟国家和中国可以一起发展国际法中的中立思想和制度,彼此在发展地区和平发展的国际法体系上也能做很多。总之,现在到了我们超越西方的中国学和东南亚学,真正立足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从我们自身来思考我们共同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候了。现在双边合作的实践成果已经很多,但是共同的知识和理论成果却显得滞后,所以学者有这个使命去弥补我们合作的共同知识这块短板。
(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6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举行的中国东盟对话关系25周年会议上的发言。)
|